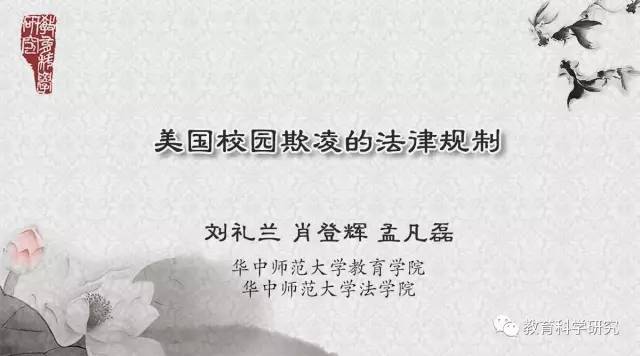
摘 要
校园欺凌行为威胁学生人身安全,妨碍正常教学秩序,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恶劣影响,现已成为全世界校园治理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美国是世界上较早以法律规制校园欺凌的国家,分别通过联邦层面和州层面的法律对校园欺凌问题做出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同时,又从司法角度为受害者寻求司法救济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渠道。这给我国治理校园欺凌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与学习的经验。
关键词
校园欺凌;法律规制
校园欺凌问题一直是全世界校园治理中的难题。据美国调查数据显示,欺凌受害者中有90%是四至八年级学生;80%的成年人在上学期间遭受过欺凌;平均每7分钟就有一个孩子被欺负。[1]对此,美国教育界曾尝试以各种方法制止欺凌,虽然在显性的身体欺凌治理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校园欺凌方式日趋多样,伤害也愈加严重,尤其是网络欺凌的出现,更加大了校园欺凌治理的难度。[2]校园欺凌的蔓延已远非教育领域可以遏制,立法规制校园欺凌越来越受到各国关注。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开始立法规制校园欺凌,现已形成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制度。分析美国校园欺凌的法律规制,可为我国以法律规制校园欺凌提供借鉴。
一、校园欺凌概念的法律界定
法律概念是构成法律的基础,以法律规制校园欺凌的第一步便是准确界定校园欺凌的内涵和外延。在美国,联邦与各州都有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各官方机构对于“欺凌”的定义也各不相同。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The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Human Services)认为“(校园)欺凌是学龄儿童间的一种不受欢迎且具有攻击性的行为,这种行为会反复发生或具有反复发生、长时间持续的可能,而且伴随事实上或明显的力量不平衡。”[3]这一定义概括了校园欺凌的两个显著特征,即行为的侵害性和行为的反复性或持续性。而美国教育部民权办公室(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Office for Civil Rights)则认为“欺凌”等同于“骚扰”,是指“一种可能以多种形式发生的,会对人产生身体上的威胁、伤害或者羞辱的行为。具体而言,行为形式包括言语行为、起外号、文字描述、使用手机和网络通信或者其他形式。骚扰不一定要有伤害意图,不一定要针对具体目标,甚至不要求具有反复性。”[4]该定义在指出欺凌行为有害性的同时又列举了欺凌的具体表现形式,有利于实践中的具体操作,但其不足之处是对反复发生这一要素不做要求,致使欺凌概念宽泛化。在新泽西州2011年施行的《新泽西反欺凌法》中则以“骚扰、恐吓或者欺凌”的概念来重新定义“欺凌”:“骚扰、恐吓或者欺凌是指发生在校园或者任何具有教学功能的领域,或者校车和校外其他场所的以手势、文字、言语、身体动作或任何电子通讯,基于种族、肤色、宗教信仰、出身、性别、性取向、性别身份和情感、智力、身体或神经的残疾等事实或可觉察的特征而做出的一个单一或者一系列在本质上扰乱或干扰了正常教学秩序或者其他学生权利的事件。”[5]《新泽西反欺凌法》的欺凌定义较为复杂,但该定义最显著的特点是明确指出了欺凌发生的原因和场所。
不同主体定义校园欺凌的侧重点虽有所不同,但总体看,校园欺凌一般具有以下特征:(1)欺凌行为的侵害性。侵害性是校园欺凌的主要特征,也是有必要以法律规制校园欺凌的原因。校园欺凌最直接的危害是给受害者造成身体伤害,轻则为一般的皮外伤,重则可致受害者残疾甚至死亡。除此之外,校园欺凌还可能给受害者造成永久性的心理创伤。(2)欺凌方式的多样性。科技发展使校园欺凌突破了言语行为、身体动作等传统的欺凌表现形式,呈现出多样化趋势,以电子通讯、网络等手段实施的新型欺凌不仅危害大、扩散快,且具有更高的隐蔽性。(3)欺凌行为的反复性或持久性。校园欺凌不同于一般的骚扰行为或偶尔的、随机的冲突行为,校园欺凌一般会在一段时间内反复发生或有可能长时间持续,会对被欺凌者构成一种长期的威胁。(4)欺凌行为发生地与学校有关联。校园欺凌主要发生于学校,但不限于学校,也可以辐射到其他与学校或教学有关联的场所。(5)欺凌者与被欺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力量不平衡。被欺凌者多为弱势群体或者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总之,在界定校园欺凌时应该立足于以上几个特征,以校园欺凌的实质危害为基础,兼顾校园欺凌的其他特点。
二、美国法律对校园欺凌的规制
美国在校园欺凌的法律规制方面起步较早,目前已形成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制度。在联邦层面,有关校园欺凌的法律规定散见于多部法律之中;而在州层面,各州都制定了自己的反欺凌法。另外,法院的判例对联邦法和州反欺凌法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一)联邦法对校园欺凌的规制
联邦法中有关校园欺凌的规定多为抽象的、一般性的保护条款,主要通过平等保护个人权利和反歧视、反骚扰来间接实现对校园欺凌的规制。例如,联邦宪法1968年第十条修正案第一款和联邦宪法1971年第五条修正案分别从平等保护权利和正当法律程序两个方面规定了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都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被非法剥夺。[6]以宪法条款确定对个人权益的保护,体现了国家对个人权利的重视,这两条修正案直接肯定了个人合法权益的不可侵犯性。之后的“1983条款”又规定,“任何个人……促使或导致美国公民或其他在司法管辖内的个人的……任何权利、特权或豁免被剥夺,将在任何普通法诉讼、衡平法诉讼或其他适当法律救济程序中对受害方承担责任。”[7]此条款为个人权益受侵犯时寻求法律救济与索赔提供了宪法依据。联邦宪法中的这几条规定确立了对个人权益的普遍保护与救济,在各州有关校园欺凌案件的诉讼中多次被引用,成为规制校园欺凌的重要法律渊源。
与联邦宪法的平等保护权利不同,联邦的另外几部法律则从反歧视、反骚扰角度规定了对个人权益的保护。2010年,美国教育部民权办公室曾指出学生的不当行为不仅违反了学校的反欺凌政策,也有可能触犯联邦的反歧视法律。[8]1964年的《民权法案》第六条规定“在美国不允许任何人因为性别原因而被拒绝参加由联邦资助的教育项目或活动,或者被否认从其中获得利益的权利或被歧视。”[9]这条规定在因性别歧视引起的校园欺凌案件中被频繁引用,成为规制性别欺凌的重要依据。之后的1972年《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1973年《康复法案》第504条、1990年《美国残疾人法案》第二条、《残疾人教育法案》等分别对因种族、肤色、国籍、残疾等因素产生的歧视作出规定。例如,《残疾人教育法案》第612条要求在“最少受限制环境”中最大限度地给残疾学生、特殊教育需求学生提供与普通学生同等的教育机会,任何人不能阻碍其获得教育的权利。[10]这些法律规定成为规制基于上述原因导致的校园欺凌的重要依据。
虽然联邦法律在反校园欺凌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这些法律主要是针对歧视和骚扰问题的规定,大量不是因为性别、种族、肤色、国籍、残疾等因素遭受欺凌的受害者难以得到联邦法律的救助。另外,在使用这些规定追究学校在校园欺凌案件中的责任时都有相当严格的要求,一般是要求骚扰(欺凌)或歧视行为足够严重,以致影响学生接受教育的权利,且学校知道这些行为但消极不作为。[11]由于联邦法在规制校园欺凌方面存在明显缺陷,各州开始独立探索立法规制校园欺凌。
(二)州反欺凌法对校园欺凌的规制
州层面的反欺凌立法始于1999年的“科伦拜恩中学枪击案”。科伦拜恩中学枪击案发生后,佐治亚州率先开始以专门法律规制校园欺凌。截至2015年3月,美国共有50个州通过了不同形式的反欺凌法。[12]在这些反欺凌法中,新泽西州的反欺凌法被认为是最严厉且规定最为完善的,[13]下面以新泽西州为例简述州反欺凌法的主要内容。
《新泽西反欺凌法》要求每个学区都必须制定一个反欺凌政策,这些反欺凌政策本身就是反欺凌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州反欺凌法对政策内容作出了最低规定,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1)要求政策内容必须包含禁止校园欺凌、骚扰或恐吓的声明;(2)要求明确界定欺凌、骚扰或恐吓的定义,且定义包含的具体内容不得低于反欺凌法中的要求;(3)概括欺凌行为的主要类型;(4)欺凌的后果及救济措施;(5)有关欺凌举报的程序。[14]正是制定反欺凌政策的要求使得《新泽西反欺凌法》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对学区、学校及师生等有了更明确的指导。《新泽西反欺凌法》内容的落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在反欺凌机构设置和人员安排上,反欺凌法明确规定,学区在每所学校都要设立学校安全小组,并且由学区督导任命一名学区反欺凌协调员。学校安全小组的主要职责是预防、识别和处理校园欺凌行为,组织和参与各种反欺凌培训,并与协调员密切配合。[15]反欺凌协调员则主要负责协调和加强学区反欺凌方案的实施,协调学校反欺凌专家、学区教育委员会以及学区督导的工作,同时还要协助学区督导向教育部提供校园欺凌、骚扰或恐吓的有关数据,并完成学区督导安排的其他事项。具体到每所学校,则要求校长任命一名反欺凌专家。反欺凌专家一般由学校政策顾问、学校心理教师或者其他有相关背景的人担任,其职责主要是主持学校安全小组的工作并牵头调查校园欺凌事件。
2. 在欺凌事件报告与处理的程序上,反欺凌法作出了严格且详细的规定。在欺凌事件的报告程序上,该法要求学校所有雇员或签约服务商在目击或知晓有关欺凌、骚扰、恐吓等事件时,必须于当天口头上报校长,并在两个工作日内再次以书面形式向校长报告。校长知晓事件后应通知涉事学生父母或监护人,并与他们讨论拟采用的合理建议或者其他干预措施。而在欺凌事件的处理程序上,该法规定得更加细致。首先,调查须由校长或者校长指定的人在校长接到有关欺凌事件报告后的一个工作日内发起。对欺凌事件的调查应当由一名学校反欺凌专家领导实施,校长可以指定反欺凌专家以外的人协助进行调查。调查应该自校长接到书面报告之日起的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如果十个工作日结束时,仍有影响事件调查结果的信息未收到,反欺凌专家则可以在形成的调查报告中进行反映。其次,调查结束后的两个工作日内要将调查结果报送学区督导,学区督导可以决定采取干预措施或建立培训项目来减少欺凌、骚扰或恐吓事件的发生,也可以根据调查结果决定强化学校安全环境、加强学校纪律建设、提供秩序咨询或采取其他合理措施。最后,调查报告及学区督导所采取或建议的措施应当在学区教育委员会例会之前提交学区教育委员会。[16]
3. 在人员培训、资金支持等问题上,反欺凌法规定对于与学生有密切联系的学校雇员和志愿者,学区必须为他们提供有关预防欺凌、骚扰或恐吓的培训。[17]在州教育部网站上,应开设预防欺凌的网络课程,课程内容应当包括欺凌预防、相关法律知识以及教育部认为必要的其他内容。[18]而且,从2012—2013学年开始,该法案还要求所有教师资格申请者都要完成预防欺凌的培训课程。[19]在资金支持上,该法要求州教育部单独开设一个账户,成立“预防欺凌基金”用于支持学区进行反欺凌培训、打造良好的校园环境以及支付相关人员开支。
(三)判例法的补充规定
虽然联邦法和州法是规制校园欺凌的主要法源,但判例法在规制校园欺凌中的作用也不可忽视。法律的稳定性和普适性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其内容的滞后性和抽象性,在规制校园欺凌的动态过程中,成文法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空白地带,而判例法则可及时填补这些空白。
事实上,反欺凌法的修改与完善很多都是由判例推动的,甚至有些条款就直接来源于判例。[20]例如,《民权法案》第六条起初只是用来规制性别歧视问题,直到1999年在“戴维斯案”中才将该条款首次应用于同学间的基于性别欺凌的问题。[21]在该案中,五年级女孩戴维斯长期遭受同学基于性别的欺凌,其母亲多次向学校反映并要求学校采取措施制止,但学校始终未对其已知晓的欺凌行为采取任何制止措施。在该案的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指出,根据《民权法案》第六条规定“在美国不允许任何人因为性别原因而被拒绝参加由联邦资助的教育项目或活动,或者被否认从其中获得利益的权利或被歧视。”该校作为一所公立学校,接受了联邦资金的资助,有义务保护学生在学校、校车、田径场或其他与学校有关的场所免遭基于性别的欺凌,但该学校在接到戴维斯遭受欺凌的投诉后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制止欺凌行为,致使原告处于一种充满敌意的校园环境里,剥夺了原告从学校教育中获得利益的机会。因此,判决该校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自此,最高法院对此案的判决为其他法院处理类似欺凌案件提供了司法依据,其他法院在审理涉及性别欺凌的案件时基本上也都遵循了这一判决的精神。
三、校园欺凌的司法救济
校园欺凌的受害者在寻求司法救济时,主要针对两类主体提起,即欺凌行为的实施者和负有监管职责的主体。[22]欺凌行为是致使受害者遭受伤害的直接原因,因而欺凌实施者必然是承担法律责任的第一主体,其承担的责任主要有纪律处分、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三类。首先,校园欺凌实施者可能会被给予纪律处分,例如,在《新泽西反欺凌法》中就规定任何实施欺凌行为的人都将被处罚,情节严重的将有可能被停课或开除。其次,校园欺凌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侵权行为,受害者也可以根据州侵权法的规定起诉校园欺凌实施者,要求其对损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另外,美国各州法律都规定了父母对未成年子女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大多数州在赔偿额度上都有限制,即一般在800美元到2500美元不等。当然,不同州对赔偿额度的限制是不同的,例如《康涅狄格州民法典》规定,未成年人故意或恶意损害他人财产或伤害他人人身的,父母与未成年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损害赔偿可高达500万美元。[23]最后,校园欺凌行为造成严重伤害时可能构成犯罪,校园欺凌实施者将承担刑事责任。在刑事责任方面,美国法律并不对未成年人提供绝对保护,当未成年人犯了成年人所犯的罪时就不再被当作孩子看待,而将会以成年人的身份对其所犯的罪行负责。[24]不同的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般由专门的司法机构通过特别的司法程序进行审理。
校园欺凌的受害者还可通过起诉负有监管职责的主体获得司法救济。在美国法律中,对校园欺凌负有监管职责的主体可分为两类,即学校和反欺凌责任人员。学校承担法律责任的法理基础是学校对学生负有监管和保护的义务,学校处在保护欺凌受害者的特殊位置上,其承担的法律责任主要是民事赔偿责任。当学校对欺凌造成的伤害存在故意或过失时,就可能会被判以高额赔偿。例如,“海德伯格案”中,学校因过失而未采取措施制止校园欺凌,致使受害者海德伯格的胳膊和大脑神经受伤,最终学校被判决赔偿受害人400万美元。[25]与学校承担责任的形式不同,反欺凌责任人员承担法律责任包括纪律处分和民事赔偿两种。例如《新泽西反欺凌法》规定,任何反欺凌责任人员在收到有关欺凌的举报后,没有及时启动调查程序,或者在知晓欺凌事件后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降低或消除欺凌危害,都将受到相应的纪律处分。而具有报告义务的人员没有履行职责时,不但会受到纪律处分,还可能承担民事赔偿责任。[26]但如若负有报告义务的人员按照反欺凌法规定的报告程序进行了报告,则可以免于民事赔偿。对于反欺凌责任人员的具体范围,《新泽西反欺凌法》包含较广,学校行政人员、教师、基于合同为学校提供服务的校车司机、保洁员、食堂员工、校医、心理专家等都在其中。
四、美国规制校园欺凌的启示
针对校园欺凌,美国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法律规制体系。在规范保障方面,州立法机构通过了专门的反欺凌法,同时也要求各学区制定具体的反欺凌政策,形成了以联邦法和州反欺凌法为主体、判例法为补充的保障体系。在司法保障方面,联邦法院和州法院两大法院系统为受害者寻求司法救济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渠道,使受侵害者的权益能够得到保障。美国反欺凌的实践经验为我国规制和解决校园欺凌问题提供了如下启示。
(一)准确界定校园欺凌的法律概念
通过分析美国校园欺凌的定义可以发现,美国对于校园欺凌的界定很多都采用了归纳和列举相结合的方法,既抽象地归纳了校园欺凌的主要特征,又具体地列举了校园欺凌的常见表现形式,从而保证了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相比之下,虽然我国已认识到校园欺凌的危害性,但官方尚未对校园欺凌进行准确权威的法律界定,这也成为我国规制校园欺凌的一个障碍。而且我国现有的对欺凌的定义也过于笼统,且偏重于感性的认知。例如,在《反校园欺凌共识》中定义“欺凌是学生遭受与自己有某种关系的同校或外校学生心理、身体上的攻击,从而造成精神痛苦的事件。”[27]因此,在界定校园欺凌概念时应立足于实践并结合校园欺凌的特征,唯有如此才能为校园欺凌的事实认定提供法律依据。
(二)完善规制校园欺凌的法律法规
校园欺凌的治理非一朝一夕之事,必须形成长效机制,将校园欺凌行为纳入法律约束范围内,从法律的高度对校园欺凌进行规制。近些年来,我国校园欺凌频繁发生,而多数校园欺凌被视作学龄儿童间的无恶意的冲突摩擦,即使造成伤害也多被当作意外事故低调处理,最终以调解赔偿了事,只有极少数造成严重后果的才会进入司法程序。这种低调的处理办法既显示出责任追究的无奈,也反映了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现阶段,我国法律并未对校园欺凌问题作出专门规定,相关法律中涉及校园欺凌和学生权利保护的条款也多是从保护未成年人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角度进行规定的。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未成年人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平等的享有权利。”[28]这些法律虽然对未成年人起到了一定保护作用,但并非专门针对校园欺凌问题,而且这些法律立法时间较早,很多校园侵权行为并未纳入规制范围,在规制校园欺凌的实践中显得力不从心。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可以在现有的法律中增设有关校园欺凌的条款或要求行政部门先行制定反欺凌规章或政策,待到时机成熟时再颁布一部专门的反欺凌法。
(三)明晰校园欺凌处理的程序及职责
以法律规制校园欺凌必然会归结到事件的处理,因此必须明晰校园欺凌事件的具体处理程序及职责。由于校园欺凌大多发生于未成年人间,经常牵扯到个人隐私,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考虑必须规定相对独立的处理程序。首先,可以以学校为单位设立专门的校园欺凌处理机构或处理岗位,由其统一受理有关校园欺凌的举报,在对举报进行判断、调查后可做出初步的处理意见。其次,可以在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内设立专门的反欺凌科室,由其受理对学校处理结果不服的申诉并直接处理学校上报的较为复杂或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同时,由其负责联系司法部门,配合司法部门做好构成犯罪的校园欺凌事件的处理工作。最后,除了专门的反欺凌机构和人员外,教师、班主任、校长等在反校园欺凌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立法也有必要明确上述各主体的具体职责。另外,职责的履行离不开责任的承担,对负有特定职责的主体必须规定具体的惩处措施,绝不纵容任何懈怠责任的行为。
注释:
[1] Atrium society,Bullying statistics[EB/OL].(2005-01-15)[2016-08-24].http://www.atriumsoc.org/pages/bullying statistics.html. [2] Rigby,K,& Smith,P. K. Is school bullying really on the rise?[J].Social Psychology of Education,2011,14(4):441-455. [3][4][8][11][25] Brookshire,J. Civil liability for bullying:how federal statutes and state tort law can portect our children[J].Cumberland Law Review,2015,45(2):351-394. [5][15][16][17][18] The New Jersey Anti-Bullying Bill of Rights Act(P.L.2010,c.122)[EB/OL].(2010-01-05)[2016-07-16].http://njleg.state.nj.us. [6][7] 米基·英伯,等.美国教育法[M].李晓燕,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436-437、424. [9][19] Norgard,H. Pushing schools around:New Jersey’s Anti-bullying bill of right act[J].Seton Hall Law Review,2014,44:305-338. [10]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EB/OL].[2016-07-11].http://idea.ed.gov/explore/view/p/%2Croot%2Cstatute%2C. [12] Bullying Police USA[EB/OL].(2015-03-15)[2016-07-11].http://www.bullyingpolice.org. [13] The New Jersey Anti-Bullying Bill of Rights Act[EB/OL].(2014-07-01)[2016-07-17].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 New JerseyAnti-BullyingBillofRightsAct. [14] Bullying[EB/OL].(2011-11-02)[2016-07-10]. http://www.edlawcenter.org/issues/bullying.html. [20] Holben,D. M,& Zirkel,P. A. School bullying litigation: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ase law[J].Akron Law Reveiew,2015,(47):299-328. [21] Kosse,S. H,& Wright,R. H. How best to confront the bully:should title IX or anti-bullying statutes be the answer?[J].Duke Journal of Gender Law & Policy,2005,(12):58-59. [22] Duncan,S. H. Restorative justice and bullying:A missing solution in the anti-bullying laws[J].Criminal and Civil Confinement,2011,(37):267-298. [23] 吴纪树,马莹莹.英美法的未成年人侵权责任承担规则[J].学理论,2013,(22). [24] 康树华.青少年犯罪与治理[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2-3. [26] 方海涛.美国校园欺凌的法律规制及对我国的借鉴[J].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6,(2). [27] 反校园欺凌共识[J].教育科学研究,2016,(2). [28]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EB/OL].(2012-12-05)[2016-07-18].http://www.chinalawedu.com/new/201212/wangying2012120516190633465538.shtml.(责任编辑:龚杰克)
论文来源于《教育科学研究》2017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