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版《陶行知全集》编辑出版前后——访《全集》副主编董宝良教授
作者简介:刘来兵 华中师范大学教院讲师,教育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湖北红安干部学院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研究。
1983年底,经过秘密而紧张的编辑,《陶行知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学术界称为“湘版”)第一卷编辑完成,初稿由全集副主编、第一卷主编董宝良教亲自送至湖南教育出版社。


“湘版”《陶行知全集》
1984年初正式出版,其后,新华社、《人民日报》、《新华文摘》等媒体发表评论文章,祝贺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陶行知全集》。全集获1986年全国优秀畅销书奖、1988年全国第一届优秀教育图书特别奖、1994年第一届国家图奖。
值《全集》出版30周年之际,笔者(以下简称“刘”)通过口述史的方式对全集副主编、原湖北省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华中师范大学董宝良教授(以下简称“董”)进行采访,求证全集编辑的缘起、过程以及背后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问题一
刘:董先生,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自20世纪50年代初被批判之后,有关陶行知本人的事迹及其研究成为无人敢碰的禁区,请问陶行知研究是在何种情况下解禁并掀起研究的热潮的?
董:你刚才讲到《陶行知全集》出版之后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事实。‘为什么《全集》出版之后有这么大的反响,我认为不是因为我们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所造成的。当时教科所是刚成立的单位,主编杨葆焜所长和担任副主编的我在当时学术界也没有什么名气。那么,最主要的原因必然是陶行知本人巨大的社会影响。陶行知是一位卓越的人民教育家,生前死后起伏特别大。起的时候,就是毛泽东说的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在教育界的位置无人能及。落的时候是在批判武训的时候,打他一棍子,从最高处跌落到最低谷。后来我们知道,这是江青一手策划的,借批判武训来打倒陶行知在教育界的影响力。

(《武训传》是由孙瑜执导,赵丹、黄宗英等人主演的一部剧情片。影片讲述了武训”行乞兴学”的感人故事。)
在电影《武训传》播出后不久,江青组织了一个调查团到武训的家乡搞调查,写出了几万字的调查报告,给武训扣上“大流氓”、“大地主”的帽子,目的是打击陶行知。关于这件事情现在网上都看得到,但在当时没人知道江青的用意。不仅陶行知在这次事件中被打倒,所有的陶门弟子,以及搞陶行知研究的都受到打击。这个事件不仅是教育上的,文艺上的,还是政治上的。“四人帮”被打倒,“文革”结束后,陶行知得到平反。但陶行知研究在两三年的时期内还是很少有人敢公开研究的领域,也就是虽然解禁了,但还没有“破冰”。发生转机的是1981年纪念陶行知诞辰90周年大会,邓颖超在开幕式上指出:我郑重地指出,陶行知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由教育救国走上民主革命道路的一个典范。冶她承认陶行知是人民教家、民主战士。因为邓颖超的讲话,就公开给陶行知全面地平反,这为陶行知研究的“破冰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信号。所以我认为陶行知本人的社会影响以及教育贡献是《全集》出版获得诸多荣誉的根本原因,并不因为是我们编的。我们只是顺应时代潮流,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我们作为编者,为陶行知研究事业也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的。
问题二
刘:《全集》的编辑工作是如何发起的?华中师范大学是如何与湖南教育出版社建立合作编辑出版意向的?
董:《全集》的编辑工作是在内因与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发起的。首先,与领导的重视有关。1982年暑假,湖南教育出版社李冰峰社长找到我们华中师范学院(1985年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的领导,他提到出版《陶行知全集》的计划,想请我们华中师院来负责主编。为什么李冰峰会找到我们呢?可能知道我们有个陶行知研究的课题。1981年的时候,我和喻本伐到上海等地调研,在上海遇到陶行知的学生杨明远,他当时主编了八套陶行知有关的图片,我们观看了他搞的图片展,他将第八套图片送给了我。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成立湖北省陶研会,只有湖北省教育史研究会,
我当时是副会长兼秘书长,因此借教育史研究会搞了一个陶行知图片展览,后又编辑了一本《陶行知纪念文集》的小册子。

这在当时反响很大,虽有非议,但后来我们才知道正是这本小册子引起了湖南教育出版社的注意,最终决定委托我们来编《陶行知全集》。当时科研处处长是邓宗琦,后来还担任我们学校的副校长,他是学数学的,但他对学术研究的嗅觉特别灵敏,也知道我们所里做过陶行知有关方面的研究。他就把李冰峰请来教科所具体安排编辑工作,跟我们介绍湖南教育出版社要出版《陶行知全集》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邓宗琦出面是有我们校长刘若曾的支持,他是湖北省教育学会的会长,我是副会长。我们就与湖南教育出版社敲定了合作编写出版全集的事宜,我们负责编辑,出版社负责出版。这就是陶行知全集编辑的内外因。有了学校领导的全面支持,也有出版社的出版任务,我们就开始着手编辑工作。
问题三
刘:据我了解,当时教育界还没有出版过一位教育家的文集,请问您是如何主持编辑工作的?
董:关于陶行知全集怎么编,这是接到任务后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确定编辑体例。我们都没编过全集,不知道按照什么体例来编,当时公开出版的只有《鲁迅全集》、《列宁全集》可以参考,这两本全集都是编年体,我主张用编年体来编。杨葆焜所长和我商量后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周洪宇具体去拟定编辑凡例,他是历史系科班出身,只有他能胜任这个任务。周洪宇在研究了《鲁迅全集》之后,建议从历史的角度,以陶行知思想的演进为基本脉络、以分类体与编年体相结合的方式作为我们主编陶行知全集的编辑体例,我们都认可这个方案。但是陶行知的学生戴自俺和陶晓光的观点和我们不一样。他们说陶夫子生前自己编了一些资料应保持历史原貌,不能拆开重新编辑。我坚持采用编年体,如果原有的资料不拆开我就编不了,不管是《斋夫自由谈》还是《中国乡村教育改造》等,很多陶行知的文章都没编进去。

我们通过曹先捷编辑把他们的意见给驳回去了,就按照周洪宇拟定的体例标准来进行编辑。其次,开始搜集资料。后来成立编辑委员会,这里又有矛盾,陶晓光提出让戴自俺担任总编。我说主编和副主编都不是我定的,是编委会和我们学校领导定的。由我们教科所的所长和副所长分别担任主编和副主编,也就是杨葆焜教授和我,我当时还是副教授,编完才是教授。我说我要向学校汇报,学校领导对我们全力支持。我们请陶行知夫人吴树琴担任顾问,这又引起陶晓光的不满,因为他觉得自己只担任委员。当时我们也不清楚吴树琴不是陶行知的原配夫人,陶晓光和吴树琴之间有矛盾。给他当了编委他有意见,但吴树琴很支持我们,把和陶行知之间的信件都给我们。陶晓光找我们要信件,我们只给了一部分,但陶晓光不依,我给陶晓光做工作,说《鲁迅全集》里就有鲁迅与许广平之间的爱情信件,这没有影响鲁迅的形象。这样才消除了各项矛盾,使得全集编辑的准备工作就绪。别看编委会成员一大群,但实际做事情的也就是我、周洪宇、喻本伐三人,后来还有李红梅也参与进来。周洪宇和喻本伐当时都是刚毕业没多久的大学生,他们为全集的编辑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也作出了很大的牺牲,没有他们的支持与付出,《全集》是很难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完成编辑出版工作的。
问题四
刘:《全集》编辑的过程一定是非常的艰辛,能否分享一下其中的故事?
董:我担任第一卷的主编,提出陶行知全集编辑的三个步骤:一是搜集资料,二是调查研究与分析整理三是开展深入的陶行知研究。首先是进行教育调查。我认为不仅是《陶行知全集》需要调查,任何研究首先都要搞一个历史性的教育调查。我们没有晓庄、育才的得天独厚,我们只有我们的人力资源,我们要把陶行知在晓庄、育才、工学团所有的活动情况和他写的东西都搞来,采取这么几个办法:一个就是我们去调研,第二就是我们做工作,请来一些陶门弟子,让他们验证,分析准不准,也可能他们自己还带来一些材料。具体时间也不清楚的,当时估计是1983年暑假前后,到南京调查。我当时有一个想法,即使调查没有,我们心里也有底。按照陶行知生前在哪就到哪去找资料应该没错。我们就去陶行知的母校金陵大学去一下。当时觉得时间紧,可能没办法都搜集齐全,基本原则是我们不能漏掉最重要的文章,包括没有署名的文章。不搞一篇假的,不漏掉一个重要的,以陶行知的求真精神来编全集。不过不巧的是,我们去正赶上南京大学(原金陵大学)搬家,不接待。我们就说从武汉来的,等你们搬家几个月后再查,时间上实在接受不了。在我们的坚持下,他们同意将《金陵光》找来,我们一看,有十几篇陶行知的文章,而且是文言文写的。

(《金陵光》学报,月刊,1909年12月创刊,是金陵大学重要的学术刊物,也是我国最早的大学学报之一。)
陶行知后来都写白话文,大众化的,老妈子都听得懂的。但是从来没人知道他写文言文,连他的学生都不知道。当时我们也没有复印机、录音机,全靠手抄。我们都是风尘仆仆地过来的,管不了其他的,就坐在走廊上抄录。虽然汗流浃背,但是很高兴。《全集》的前几篇都是这里查到的。这些作品公布出来之后,学术界尤其是陶研弟子都很惊讶。都知道陶行知古文功底好,但没见过陶行知写古文。这文章里面没有标点,都是我标出来的。为什么我们有贡献,是为研究陶行知提供了丰富的全面的第一手的资料。第二次调查我们还有一个收获,我一个人中途单独到合肥文化馆,把陶氏族谱调出来了,很多争论不休的问题就是靠族谱解决的。
问题五
刘:可以看出,您和其他几位编辑人员在《全集》编辑的过程中付出了极大的努力,除了四处奔波查阅资料的辛苦之外,恐怕在精神上还得承受很大的压力吧?以当时的情况,《全集》的编辑工作可以是公开的行为吗?
董:确实是这样,尽管陶行知研究已经解冻,但可能还会出现反复的情况。因而我们编《全集》还是非公开的状态,担心有人揭发,那可是要犯政治错误的,不仅是我们几个编辑,恐怕连学校都要受到牵连,所以只有出版社和校领导知道我们在编《全集》。我们走访调查、搜集好资料之后要集中地方来编写,在哪里编呢?肯定不能在学校里面编。请示过领导之后,领导给我们提供支持,最后确定到汉口车站一家旅社里面做编辑工作,白天上班,晚上回家,谁也没敢告诉,就这样在旅社里关了几个月,第一卷编完了。我们当时还有个编辑叫李红梅,也参与了部分编辑工作,熊贤君参加了校对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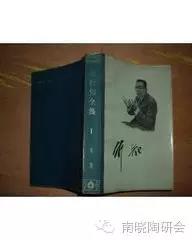
《全集》编完之后,需要将稿件送到出版社。那时候不像今天,发个电子邮件就可以,需要将文字稿送到出版社。1983年底的时候,曹先捷编辑给我打电话,让赶在年底前将稿件送过去。几次送稿,都是我亲自送的。第一次送稿,我觉得书稿比自己孩子还重要,要是搞砸了后面就都砸了。坐火车到湖南长沙,一路上连觉都睡不着。很感谢学校的领导,学校的刘若曾校长特别支持编《全集》,没有他在背后支持,担任名誉主编,那是不行的。刘若曾之后,是章开沅继任校长,他对我们搞陶行知研究也是大力支持的,我们还一起合作申报了国家社科课题。后来他又支持我们成立湖北省陶行知研究会,担任会长,我任副会长,我们一起共事了十几年。
刘: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给我这个珍贵的采访机会!祝您身体健康!希望您能为当代陶行知研究的发展做更多的学术指导!
来源:南晓陶研会
编辑:赵美君


